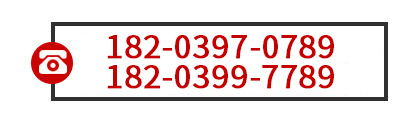他曾在西部山里修了三年铁路,也是首个通过纽约州律师资格考试的中国人,供职于顶尖的华尔街律所。
他是中国长期资金市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两进两出证监会,却自我调侃“是证监会最不受欢迎的人”。
他曾掌舵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司,操盘数千亿美元,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老师,喜欢和学生们聊天,他说“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观点起不到太大作用,我就让更多的人去,我希望影响这些人。”
近日,前证监会副主席、前中司副董事长、总经理,68岁的高西庆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回忆参与创办中国长期资金市场的经历,高西庆说,就跟今天出去创业一样,有的人比较实际,有的人比较冒险,“我就是愿意冒险的人,但是我也有实际的一面。”
1987年10月19日,美国证券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一天内股市跌掉23%,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找到在华尔街做律师高西庆和在纽交所任职的王波明,了解长期资金市场对中国的影响。
到了年底,王波明的哥哥带着国内金融改革的见闻来到纽约。“然后王波明半夜三更把我拉过去,说了好几天。白天干活,晚上就在那谈,不睡觉,很兴奋谈了三天,说应该回国去搞股票交易所。”
了解到国内情况后,高西庆和王波明在美发起设立“促进中国长期资金市场发展委员会”。“在纽约的中国人,加上七八个美国人,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律师、投行朋友,感兴趣就都来参加。大家谈了一阵子就开始写白皮书。”
白皮书全称为《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是民间有关中国长期资金市场设计的最早蓝图。
回忆起当时回国的决定,高西庆说,他未曾想过“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但“觉得中国一定会好起来,而且要靠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回国前,高西庆花了两个月时间自费走遍海外各个证券交易所,从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米兰到东京。甚至还来到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瞧了瞧社会主义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是什么样子。
1988年9月2日,一路上积攒的大量资料揣在大小箱子里,高西庆从香港过罗湖关口,再回到北京。6天后,中国股市筹建真正开始启动的标志性事件北京万寿宾馆会议(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举行。
1989年3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正式成立,1990年底,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开业,1992年10月证监会诞生,高西庆是全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个中滋味,颇为复杂。一个轶闻是,高西庆和王波明曾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干不成,高西庆去东边修自行车,王波明到西边卖包子。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生活里的苦难,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生活里我能干成的事儿,1%都不到,你必须做99%的努力。”高西庆说,“我们当时所想象的是,我们努力把这个事干成,但很可能干不成。”
既有书卷气又有“牛脾气”,充满理想主义与冒险精神,高西庆的挑战,才刚拉开序幕。
1992年,证监会成立,高西庆出任首任发行部主任和首席律师。用他的话说,是“在刘鸿儒主席的容忍之下,做了很多推动的事情”。1999年,在香港担任中银国际首任总裁的高西庆被召回证监会,时任证监会主席是周正庆,换为“老熟人”。
1993年,高西庆主笔起草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颁布,第一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股票发行的审批制,标志着进入中国股票发行制度的第一阶段:“额度管理”。即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当时的国家计委、体改委和经贸委在宏观上制定当年股票发行总规模(额度或指标),分配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国家相关部委,再由省级政府和国家相关部委在各自的发行规模内推荐预选企业。
高西庆说,他所设想的股票发行跟国外的相对一致,就是公司自己本身出去筹资,筹资应是自发的行为。而中国的市场是“从上往下”建立起来,因此当时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的色彩。但“允许股票发行”这一举动本身,已有非凡意义的进步,为企业面向社会筹资提供了机会,解开了束缚。
据高西庆回忆,对于额度的分配问题,“上面要4家来定:国家计委、体改委、经贸委,和证券委(证监会)。”但在高西庆看来,证监会不应该要这一项权力,“这跟我们的职责是冲突的,应该把它推掉。咱们不可以决定这些事,我们只做监管。”
这一观点让高西庆在当时显得有些另类,或者说有些超前。他始终主张,证监会的职能应只是“警察职能”:只管额度分下来之后公司信息公开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是否有内幕交易、是否有操纵市场,一旦参与利益分配,“麻烦”就大了。
高西庆说自己:“今天到了这个年龄,智慧稍微多了一点,认为这个很正常,当年是一定不可以容忍的。”但正是这份“觉得不能容忍”,也推动了很多事情——当年假如能提前预知要历经的困难,也许他就真早早地去修自行车、沿着爱好做无线月,高西庆以健康原因为由请辞,回到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任老师,一年多后前往香港,主持了中银国际的组建工作。当时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依赖外国投行,中银国际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在香港干得正是热火朝天,1999年一封调令,他又收拾行李回到了北京,重返证监会。那时《证券法》刚刚颁布,确立了核准制的法律地位。而核准制的第一个阶段是“通道制”。
“通道制”改变了由行政机制遴选和推荐发行人的做法,使承销总干事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承担起股票发行的风险。
“技术上的事情多了。”高西庆笑言, “券商肯定是得罪了。券商本来坐那儿收钱,结果要负这么多责任,意见当然大。”
高西庆曾参与《证券法》的制定,从1992年人大提出起草《证券法》,到1999年正式实施,花了整整7年时间,其间有诸多曲折。
“所以我后来理解,这是一个过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不同的利益,这么多不同的认知程度。”高西庆说。
在证监会的两段任期之间,高西庆曾有一整年时间,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琢磨着写出了《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理论依照》。1996年10月,该文章在证券市场导报发布。
在结论一节,高西庆写道:“中国的证券立法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强制性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及有关问题,如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及时性和可比性等问题,以及对蓄意违反信息公开披露法规的调查和处罚问题上投入最多的关注和最大的努力,以图使市场日趋成熟,最终将政府从社会成本很高、自身风险极大、吃力不讨好又烦不胜烦的日常经济决定和具体市场运作中解放出来。”
“所谓强制性信息公开披露就是指注册制。”高西庆说,“文章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说,最后一定要把发行的机制由市场来管,而不是由监管部门管。”
这一观点,在当时以行政手段决定股票是否有上市资格、以行政力量不时调节市场波动的阶段,显得很超前。
文章本身的理论性也极强,对于不少系统内的官员来说,理解难度都颇大,“绝大部分人看了就扔了”,但得到了吴敬琏教授的重视与推荐。
而注册制正式被提上议事日程,还要等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那之后又过了6年时间,注册制随科创板真正试点实施。注册制是化解过度干预等旧疾,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正是在于以信息公开披露为中心。
高西庆对注册制评价颇高,他曾在2014年公开表态:注册制是证监会近年来的最大功绩。
对于如何加强完善注册制,高西庆称,“如果从监管部门的角度,证监会、交易所他们真是做了很多工作,做到了没那么多可挑剔的地方。必须要政府最终充分意识到,一个是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一个是法治。今天回头来看,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如果按目前的路子走下去,方向应该是市场化的程度慢慢的升高,那么市场的透明度会更高,造假、欺骗的情况会得到更大遏制,违法成本会更高一些,我希望是这样。”高西庆说,“我谨慎乐观。”
澎湃新闻:您是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最早的设计者之一,怎么评价30年中国长期资金市场发展的成果?
高西庆:30年,中国长期资金市场从零发展到这么巨大的体量,是全世界都没有过。不管是从融资量、本身市场的价值、上市公司数量、从业人员等各方面,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在资本资源的配置上,有了巨大的改变,比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好了很多。但也存在着弊病。
这些弊病,目前是在逐渐解决的过程中。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易主席来了之后,我感觉易主席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性。这不光他一个人,中国政府也是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后,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当年做证监会主席的时候,我跟他搭档。说,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不能对股市的高低发声和起作用。但在那之前和那之后,有过多次政府忍不住去干预市场。现在终于认识到每次干预都要付代价,这个代价终于到了划不来的地步。
总体来说,长期资金市场这一段时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有不少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解决。
高西庆:当时我跟王波明搞了一个促进中国长期资金市场的委员会,美国人中国人都有,纽约的报纸也有点报道。我准备回来的时候,好多美国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何需要回去。我觉得很自然,因为我是中国人。
那是1988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初走的时候。他们说美国的生活更好,我说这是你们的祖先给你们创造的,我们中国人、我的父老乡亲过得还没那么好,我们要让他们过得跟你们一样好,比你们还要好。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觉得不可能。
当时对中国会变成什么样,我没明确的目标,但我觉得中国一定会好起来,而且要靠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我自己愿意做这个努力。每一次有人问我为何需要回来,我说我好像从来就没纠结过。我和王波明这批人,大家都希望改变,就回来了。
高西庆:从辩证法来讲,所有的偶然都寄寓于必然之中。所谓必然,从整个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到了此阶段,应该有新的机制出来。
偶然是因为,我从上法学院的第一年开始,每年夏天都有律师事务所愿意让我去“打工”。当时中国学法律的人很少,美国人觉得很新鲜,所以我去申请工作,(他们)特别愿意要我。我申请工作的那家事务所是尼克松当年的律师事务所,他们跟中国没有一点业务关系,但觉得有个中国人来了,这个很有意思。我去了之后,他们一看我能顶他们的人,甚至干得还要好一点,所以很愿意要我在那做,这是历史的偶然。
后来我跟王波明他们这些人认识之后,成立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这时中国人起步进入华尔街,王波明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有人在美林,有人在高盛,还有一两个人逐渐进入律师事务所。大家本来是在这方面有一些交流,但并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在美国的交流。
没想到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中国方面特别关心,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处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总领事想听一听。去才告诉我,不是总领事要听,是中央的领导要听。我听了很吃惊,我说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他们说想知道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到底有没关系,第一,在美国的机制之下这件事怎么发生的;第二,它会对世界经济有什么影响;第三,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说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对美国影响很大,对中国(影响)看不出来,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太大影响。(但)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对这个开始有了兴趣。
到了年底,王波明的哥哥,他是在加拿大的枫叶银行工作,当时回国待了几个月,经过纽约和我们说国内的金融改革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大家有各种想法。然后王波明半夜三更把我拉过去,说了好几天。白天干活,晚上就在那谈,不睡觉,很兴奋谈了三天,说应该回国去搞股票交易所。
刚开始提出这一个话题,我觉得很可笑,这些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我直接说这不可能。他说为啥不可能?他说了讲的很多事情,我觉得还真的有这种可能,就搞得很兴奋。大家谈了好几天,决定成立一个机构: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委员会。一号召,二三十个在纽约的中国人,加上七八个美国人,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律师、投行朋友,感兴趣就都来参加。
大家谈了一阵子就开始写白皮书。后来在中国较为广泛的流传的、当年得到重视的白皮书,是第二版的白皮书,第一版是我们在纽约做的。回来之后又跟张晓彬、、一块搞了第二版更正式的白皮书,直接上书到中央,得到了重视。
高西庆:困难很多,第一位的就是意识形态,第二位是财务问题,第三位是具体谁来做怎么做。
技术问题非常多,但第一位的必须要克服。因为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时要弄股票交易所,让不光要让愿意改革的这批人了解,也要使所有做决定的人都通过。
我是1988年7月30号离开纽约,我先到欧洲整整待了一个月,伦敦、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日内瓦、米兰、布达佩斯,一个股票交易所挨着一个地去看。
到了米兰,米兰交易所的人告诉我说布达佩斯也有交易所。当时匈牙利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说布达佩斯有交易所?怎会是?他们说有,上个礼拜刚派人到这儿来学习。我马上要了电话,改变所有行程,坐上火车直奔布达佩斯。结果到了边境上被匈牙利的警察抓住了,要我的签证。我说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用签证。
我是从奥地利过去的,一帮警察把列车查完之后,全部到我这一个包厢来,反复说 visa。我就说 no visa,Socialist。
最后到了布达佩斯,警察把我拉到了一个旅行社,那个人会说英文,问我来匈牙利干什么?我说我要到你们的股票交易所看一看。他们争论了半天,又把我拉到警察局给我盖一个章,我算是有了visa。然后我就直奔交易所待了一天。非常有意思,布达佩斯的交易所其实一个礼拜只开一天,买卖的都是债权,还没有股票交易。
我一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从印度孟买到了香港,又从香港到了东京,最后从东京回到香港,1988年9月2号从香港拉着大小箱子从罗湖过。
高西庆:这个就跟今天出去创业一样,有的人比较实际,有的人比较冒险,我就是愿意冒险的人,但是我也有实际的一面。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生活里的苦难,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生活里我能干成的事儿,1%都不到,你必须做99%的努力。我们当时所想象的是,我们努力把这个事干成,但很可能干不成,可能百分之八九十干不成。
我从小就喜欢动手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做收音机、各种机械,在兵工厂做机修工做了将近两年,在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学校那些老教授谁自行车坏了都喊我修。所以我想,我搞一个自行车铺应该也能赚钱,最不济我就做这个。
高西庆:我们当时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楚,也没有像今天这么世俗,当年还是充满了理想主义。
在810之后不久,朱总理当时的助手来找我、王波明、李青原几个人,说要成立证监会,希望我们都进去。
我第一反应是我不去。当时王波明很有兴趣,我说我去不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想过,我是员,像这种事肯定一马当先去做。但那时候已经回来4年了,4年里我跟无数机构、官员打交道,发现好多东西我是推不动的,很费劲儿。我这人比较直,不像有些人绕着弯子说话,所以我说我不行。
后来他们说,你们要不进去的话,得请别的人,说了一些别的人的名字。对那些人,我觉得他们来之后会把市场搞得很糟糕,因为他们是计划经济的头脑和管制的方式。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先进去,建立起来机制再出来。所以我当时说,我就干两年。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很多管理者思想非常开放。我们在刘鸿儒主席的容忍之下,做了很多推动的事情。
到了两年,我觉得差不多了,要出来。刘主席说,不行,一定要帮忙再干一段,所以后来又干了一年。到第三年我就辞职出来了,不是因为市场建成了,而是这一个市场我能够改的东西改不动,所以我就出来了。
高西庆:我们基本上借用了西方的机制。西方机制里最完整、最复杂、最能够对付各种奇怪的事的,就是美国的机制。我到全世界转了一圈,搜集了40多个国家的证券交易法规条例,发现绝大多数都是“照抄”美国的。因为美国的证券法最早出来的,美国当时长期资金市场的规模是全世界所有长期资金市场规模的60%多,其他合起来就顶他一半大。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还借鉴了一部分英国和中国香港的方式。
我第一稿写好之后,后来就“打得不可开交”。国务院法制局的人对证券这块不了解,但他们对中国整个法律机制比较了解,他们说这个过不去。为什么?第一,有的领导不理解,第二,意识形态问题,第三,法律技术上不能过等。
这砍那砍,砍掉很多,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焦头烂额,搞了好几个月,有时候很生气。现在像这种事我很理解了,当年就很容易非常生气,说这个怎么能不要。后来过了很多年,老有人来说你当年搞的啥东西,里面不伦不类的。我说你得看我们的初稿。
后来搞《公司法》,当时是厉以宁和曹凤岐两位老师,受全国人大委托,做《公司法》的起草工作,我和陈大刚这些人在证监会帮忙。我们搞出了一稿,我认为是最好的一稿。
结果到了人工委,他们另拿出一稿,照抄中国台湾、日本,拿来让证监会提意见。我们一看,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我和陈大刚一个礼拜每天几乎不睡觉,写出来十几页长的意见。
到今天,在实践过程中,《公司法》比原来好了很多。所以我后来理解,这是一个过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不同的利益,这么多不同的认知程度。
高西庆:我们所设想的发行跟国外的相对一致,就是公司自己本身出去筹资,筹资是自发的行为。但我们的市场不是自发从底下往上建的。中国基本上几千年来都是“凡是没有允许的都是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设想的发行机制当然不能实现。
但巨大的进步是,中央决定允许发行股票。因为在那之前,我们整个都是计划经济,每一年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多少钱都是有计划的,突然来一块从社会上筹钱,于是允许第一年50亿试验一下,这叫额度。
50亿拿出来之后怎么分?上面要4家来定:国家计委、体改委、经贸委,和证券委。证券委当时实际操作部门是证监会。这样总共四个部门一块决定这件事。
我跟主席说,证监会不应该有这个任务,这个跟我们的职责是冲突的,应该把它推掉,让他们决定,咱们不可以决定这些事,我们只做监管。
证监会当时也有官员是国家机关出来的,他跟我说:你昏了头了,这么重大的权力你不争取,不要这块权力就没有人理你了。
我说,为何需要有人理我?为何需要这个权力?(我)当年真的什么都不懂,不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权力。
但是就是这样,50亿拿来,然后就开始分配。上海2.5亿,北京2亿,各地一点一点分,一直到青海等,1000万额度。
我是发行部主任,当时有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发行股票是筹进来的钱按这个额度卡,还是目标要发这么多额度面值的股票。他们就来问证监会,我说就按发行股票本身,他们说是不是要跟别的几家商量,我说绝对不能商量,只要一商量,他们肯定说要按筹来的钱算,那你总共就只能筹来50亿,如果按我们这种,只要能溢价,那就远远不止50亿。
果然出去之后,中国人多聪明,每个部门马上明白,各省就开始把自己的额度无限多地细分。给他一亿,他就分成10份,每份一千万。本来公司需要一亿,发一块钱股票卖十块,一亿就进来了。
上面有领导一看,到第二年就开始说不行,要光按这个大家就会无限细分。于是就引入了两个指标,一个是额度,一个是家数。比如1亿只准两家,1.5亿只准三家。
高西庆:我在1974年到78年是工农兵大学生,当时以学习国际贸易为主。研究生我原本是学的宏观经济,学了几个月之后被领导逼着改成法律,但是我对宏观经济一直很感兴趣。当时1978年后,国外的书慢慢的变多,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进来,我们的发现跟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到国外去,学习西方的法律。他们的法律是建立在经济原则基础上。然后(我)再到华尔街工作。
他们说你怎么这么超前,我说一点没超前,这是很正常的东西。用了它的机制移植到我们这来,当然要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你的想法,可是要把它硬套进原来的窠臼里,是很难的。
高西庆:当时很多人担心这一个市场已经这么低了,有很多人情绪很很大。这些人其实对于中央决策,对于政府里面很多东西,已经有相当的影响。
当时大家对于股市的重视程度,我觉得比今天还高,忽然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个事情,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不满足于自己原来每个月30块50块钱工资的人,都想(参与)“合法合理的这种赌博”。
结果股市掉成这个样子,很多人就很紧张。我印象特别深,甚至有人说股市会不会掉成负的,我说绝对不会掉成负的。第一,负的等于把股票给你还要给你付钱,这不可能,总是有价钱的;第二,总是有人会趁机进入,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到(时候)了。我当时确实说过这个话:已经到了很低的时候,一定任何风吹草动就往回走。
因为市场已到了蓄势待发随时可能往上走的程度。大家都知道,政府只要稍微表现,“哐”地就上去了。从这以后,每一次当市场稍微有点(波动),大家就开始吹各种风。在国外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行政部门能够对经济起作用的办法非常有限。包括美国欧洲的央行,政府一般都不能有实质的干预,它只能对财政有一定干预,财政可以掌握的资源是很少的,只有税收的来源。而中国不光税收,还有各种国企。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做大量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府这边稍微有这种想法,人家琢磨透了就使劲“捅你”。这样已形成了特定的套路,在这个隧道里头你也出不去,因为市场把你琢磨透了。
高西庆:今天到了这个年龄,智慧稍微多了一点,认为这个很正常,当年是一定不可以容忍的。
但是,我想很多事情是“觉得不能容忍的人”推动的。如果当年都很清楚后果,就不一定做事了。
你要是一眼就看透了,干脆干点别的。我从小就喜欢无线电,我就开始研究无线电去算了。
高西庆:我们事实上做了很多牺牲,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到今天至少能让我吃饱饭。我自己本来就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在离开证监会之前,中国银行的领导当时希望搞一个投行,就来鼓动我出来弄这个事。中国银行是中国当年最国际化的银行,在整个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分支机构,并逐渐进入投行领域。
我说我还在证监会,得遵守我自己写的规则。我当时在证监会,制定道德守则这方面的东西,我本来写了“离开证监会两年之内不应该进入跟证券监管有关的任何领域”。领导一看说,这你让我以后还怎么招人?本来工资又给不高。我说那行,两年太长,就改成一年吧,但不能再短了。
后来我出差到美国讲课,讲了几个礼拜。等我回来,看到他们发出来的要求是三个月,把我气得够呛。我说这怎么可以,后来又改成6个月,最后当然又改回了一年。
到了1995的10月,我离开证监会,中国银行马上找到我,我说一年之内不能去。我说这规则是我写的,我要也去了,规则不就成玩笑了吗。
整整12个月,我就在对外经贸教书。最后到了1996年底又找我,我同意去。到了1997年上半年,我就到中行,以香港为主设立中银国际。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银国际成立了,我做首任总裁。我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终于有中国人自己的投行了。当年中国主要企业出去上市,都是美国、欧洲的投行在做,我们也要在这里占一席之地。到了1999年的6月,忽然就接到电话,证监会的领导说,欢迎你回来。我说啥意思,什么叫欢迎我回来?领导说让你回证监会你不知道吗?我说不知道,这谁说的?他说,你赶快去问你们中行的领导。
我去找当时中行港澳管理处的主任,他笑了笑。我问,是否有这事?他说,是有这事,不过我们正在商量你能不能跟领导讲你不去。他把抽屉拉开,把调令拿出来看,果然是。
从他的办公室回到我办公室,电话响了,是我老婆电话。当时家属办去香港(的手续)很麻烦,办了一年多,她跟我说今天早上刚通知说办成了,要带啥东西来香港。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带,就带两个空箱子来。她说你啥意思?我说刚刚通知我得回北京了。
我们这一代人,工作大多数都是被分配的,而且真的属于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的人。我说我们都是雷锋式的好干部,像螺丝钉,把我们拧在哪,我们就一直在那儿干。
今天的年轻人选择太多了,所以今天年轻人思想很发散。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创造性,我说不用着急,肯定有创造性,因为现在年轻人思想没有那么多禁锢。
高西庆:是进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证监会还有相当一批原来很强的人员,但是由于海归进来得比较多,外面就开始躁动议论,说什么海龟土鳖。
其实我当时非常反对,每次有人跟我说,我就说不许造这种舆论。我说我四十几岁了, 40多年里在美国总共只待了6年,30多年在中国,凭什么说我是海归?我比所有人都土得多,我在大山里修了三年的铁路,在社会最底层干最重的活,吃不饱饭,16岁起干了三年,然后做了将近两年工人,做最苦的活。凭什么说我是海归?好像我不食人间烟火似的。
高西庆:三个大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国有股减持的问题,因为它是解决市场一个基本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发行的问题,我希望把它尽可能市场化。在那之前限制市盈率,这实际上等于资产再分配、利益再分配的过程,限制市盈率,就把原来应该属于发行公司的利润,分到了证券交易市场这些人来,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也不合理。当然这个也有问题了,就把市盈率放开,结果一下子就达到80多倍、100倍。再一个就是市场监管的问题,大规模地增强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的监管。
高西庆:原来券商在这里面,(他们的)利益机制不一样,总是白赚钱也不管别的。我说不行,券商有能力去发现它(指上市公司)的问题,你又有足够的钱去赔偿,那好,把你拉进来。
(编注:2001年3月29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对“通道制”做出了具体解释:每家证券公司一次只能推荐少数的企业申请发行股票,由证券公司将拟推荐企业逐一排队,按序推荐。“通道制”改变了由行政机制遴选和推荐发行人的做法,使承销总干事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承担起股票发行的风险,同时也获得了遴选和推荐股票发行人的权利。)
高西庆:技术上的事情多了。后来有人给我总结出“六大罪状”:得罪了六个不同的利益方,券商肯定是得罪了。券商本来坐那儿收钱,结果要负这么多责任,意见当然大。我收到过很多威胁,有人打电话说,知道你们家在哪。
高西庆:我是1996年发表的文章《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理论依照》,所谓强制性信息公开披露就是指注册制。我1995年10月离开证监会,1996年底发表文章,这一年里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我写完之后发给所有证监会我熟悉的领导,发给各个人,绝大部分人看了就扔了。
但吴敬琏教授看了之后,就说你们要看这个文章,结果一下子,有一些人给我打电话说,证监会的人到处都在找这篇文章。文章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说,最后一定要把发行的机制由市场来管,而不是由监管部门管。
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终于说要试验注册制,这些人给我打电线年的东西终于来了。我说没那么快,一方面我非常欣慰,大家终于愿意谈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它不那么容易,因为矛盾太多了,要一点点来。
这和中国整个的公共治理机制是有关的。中国几千年来的管理机制都是:没有允许的,都是禁止的。现在开始有观念是: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上海从自贸区开始,就说搞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就这个意思,只要没有禁止都可以。
高西庆:如果从监管部门的角度,证监会、交易所这些,他们真是做了很多工作,做到了没那么多可挑剔的地方。问题不是在他们这,而是用一个原来老套的话说,我们自古以来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跟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政府功能比他们的政府功能要大很多倍。
所以在这种机制之下,想再进一步改变到大家所理解的相对充分的注册制,那是有难度的。因为社会出了任何一个问题,人们都想找一个系统负担责任,市场出了问题、证券有关的问题,总得有人负责任。
在美国,证监会是管在市场里做坏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这些,证券市场本身的涨跌,只要找不到违法的事,证监会是没有一点权力管这事的。而中国只能找证监会,我说证监会历任主席不容易干,就这个原因。
到今天,易主席上来之后,做了很多特别好的事。易主席很聪明,毫无疑问,但是易主席比别人强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于,他这个时代好,因为他到了一个各方面的领导都意识到用原来的方式管不行了(的时代)。
原来各任主席,受各方面的压力多了去了,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比你官大的地方电话就来了。
所以刘鸿儒主席退休之后,特别感慨地跟我说:很感谢你,这几年替我挡了不知多少。那会我在证监会管发行,好多官员一来,跑到他那来,就说怎么样,他就说没问题,我肯定愿意,不过我们这的发行部主任,他是一个美国律师,很麻烦。他们就找我,我就给人堵住了。
别人跟我说威胁你了,我说没关系,我不怕。我这人是“三等残废”,我修铁路的时候脑震荡,脑袋整个砸开花,昏了半个小时,流了上千CC血,我这命也不值钱,他威胁就威胁,真的没关系。
必须要政府最终充分意识到,一个是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一个是法治。但这个是一个过程。今天回头来看,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还得有很久来落实。
高西庆:我一直说的是,证监会所有的职能应该只是警察职能,而不那么多别的方面和多元化的目标。你给多元的目标,没有人能干得好的,谁能干得好?同时手里拿着8个球颠来颠去不让掉地上,是不可能的事。
当年我就说那话,(股票发行额度)你让国家计委去分,让财政部分都可以,证监会就只管在这分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只管分下来之后公司信息公开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是否有内幕交易、是否有操纵市场,这些事情是全世界所有的监管部门应该做的。但是如果一旦进入利益分配机制,你要决定人家能不能赚钱,你要决定资源能分配给谁,麻烦就大了。
证监会工作人员的水平能力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相比都算很强,因为我去过几十个国家的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我后来在社保和中投,到了每个地方出差,有机会我还会跟他们之间聊一聊,不光是工作有点联系,主要是我有必要了解它机制的运转。所有这一些地方管理人的水平,没有哪比证监会的人更高。美国的水平是相对最高的,咱们也都差不多,但是他的目标非常单一,他所要做的事情很直接,所以他可以做他的事。
高西庆:我是谨慎乐观。如果按目前的路子走下去,方向应该是市场化的程度慢慢的升高,那么市场的透明度会更高,造假、欺骗的情况会得到更大遏制,违法成本会更高一些,我希望是这样。
但是回潮的可能性还是有。比如觉得不行了还得管,政府只要再使劲去管,那么给市场又造成一次概念的强化:政府对这一个市场,就是要管理干预的。这样市场长期投资理念就很难建立起来,所以我谨慎乐观。
我这辈子干了无数不同的工作,光修铁路期间,就做过大概七八种不同的工种,最粗重的扛水泥,扛石头,做测绘,扛测绘杆,架高压线,盖房子,每一样工作我都努力去做到最好,哪怕最简单的工作,我会去琢磨有哪些办法是最省力,效率最高。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观点起不到太大作用,我就让更多的人去。学生群里,我都要发很多带有强烈观点的东西,为什么?我希望影响这些人,我发现这个是有作用的。有很多学生都毕业好多年了,时不时还来找我聊天。哪怕有一个学生,我对他有影响,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高西庆:他们知识层面的东西,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你不做违法违规的事,不做违反道德的事,头顶三尺有神明。你不能觉得人家看不见你就能怎么样。这么多年,能想象我所看到的这些人有多少。少数人我不奇怪,当年可以感觉出来。多数人我都觉得可惜,很聪明很能干的人,各方面都很强的人,但是就会栽在诱惑里。别有任何侥幸心理。
我在证监会第二期的时候,经常要让我讲讲课,我就说避免瓜田李下。瓜田李下啥意思,就是哪怕有一点怀疑都别做。人家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说你别在河边走行不行,你离远点,瓜田李下的事你别做。
另一方面的原则,作为一个投资者,基本的原则大家都明白。我跟巴菲特见过很多次,巴菲特的道理都是很直白的,人一听就明白,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他说对了,但是别人就实行不了。为什么?就是贪心。他说,所有人都在贪婪和恐惧之间摇摆,他说他就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他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就是用跟别人完全相反的方式做事的策略,其实我觉得这不是策略,是一个原则:你不能那么急功近利。
多数投资者,甚至包括机构投资的人都急功近利。其实看透了,做更长期有很大好处。大原则你要坚持住,该断臂的时候断臂,该坚持就要坚持。但现在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短期的进进出出的行为。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习。中国的股民中等水准在技术层面上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股民水平都高,但是不去研究更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一些大的宏观条件。
这是个双向的东西,如果一方面监管部门的人他不去干预,现在我们的监管部门已经越来越少干预。另一方面我们股民慢慢的变多地看长期。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这样中国股市慢慢就会变成长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