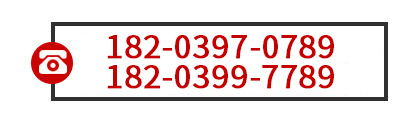《技术陷阱:自动化时代的资本、劳动力和权力》一书以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史为线索,将各个时期的技术发展与相应的经济、社会状况概括为“大停滞”“大分流”“大调平”“大反转”等阶段。作者觉得技术的类型对工人的命运起着关键作用—“劳动力替代型技术”使工人被机器取代、工资收入下降、政治不稳定加剧;“赋能型技术”则促进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工资收入增长,从而促进社会稳定良性发展。作者提出我们该从历史中学习经验,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应对当下及未来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本书为读者详实地展示了历史进程中的技术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和工人命运的广泛关联,也为当下我们面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挑战提出可行的应对方案。
近年来,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就业和工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技术陷阱:自动化时代的资本、劳动力和权力》(The Technology Trap: Capital, Labor,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以下简称《技术陷阱》)从历史的维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该书一经出版,便被评为了《金融时报》年度最佳书籍,并被列为芝加哥大学推荐必读书目。作者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ct Frey)是经济史学者,在牛津大学马丁学院主持名为“工作的未来”研究项目,被认为是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自动化影响的学者之一。事实上,最早让弗雷声名大噪的并非《技术陷阱》一书,而是其于2013年与牛津大学工程学学者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共同发表的论文《就业的未来:工作如何受到计算机化的影响?》。在该文中,两位作者通过一系列分析计算美国劳动力市场上702项工作被计算机取代的可能性,预测未来20年内47%的工作将面临高度被取代的风险。[1]文章发表后即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了相关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相较而言,《技术陷阱》更强调从历史维度做多元化的分析,通过对大量的史料和数据的考察,向读者展示了一部浩瀚的技术进步与工作变迁史。作者觉得应向历史学习,并以此预判未来的产业和工作形态变迁,提出政策导向的建议。
《技术陷阱》一书以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史为线索,将各个时期的技术发展与相应的经济、社会状况概括为5个阶段,即本书的5个核心部分:“大停滞”(前工业时期)、“大分流”(工业革命时期)、“大调平”(电气化时期)、“大反转”(自动化时期)、“未来”(人工智能时期)。[2] 贯穿5个时期的核心线索是:技术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对工作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和工人收入的影响,技术的触角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所谓“大停滞”,指的是在工业革命前,全球人均GDP经历了长期的增长停滞,直到1800年左右,即工业革命后才以惊人的方式开始起飞。花费大量篇幅讨论工业革命发生前数千年历史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弗雷指出技术的进步并不是从工业革命时期才开始的,在前工业时期的不同阶段同样存在着很多技术发明。一些技术发明原本有望极大地促进生产力但最后却没有被推广采纳;另一方面,弗雷也还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技术能否得到推广和发展,并非取决于技术本身的优劣,而是与当时统治阶级的意愿、政治力量的分布、劳动力供给情况等诸多因素相关联。
弗雷通过大量的例子阐释了他的观点,其中一个例子援引自史学家苏尔托尼乌斯(Suetonius)。众所周知,罗马帝国时期的帝王们均热衷于建设各种大型宫殿和宏伟建筑,也因此耗费大量劳力。其中,维斯帕先大帝曾拒绝了一项技术发明,该装置能把巨型柱子从石头矿场运送到罗马的建筑工地,可节约数千劳力。维斯帕先大帝拒绝使用该装置的理由是,使用装置后就没有工作提供给他的子民让他们糊口了。[2]40这并非出于仁慈,而是因为统治者深知,通过提供工作机会让工人得以养家糊口,才能维持社会安定、维护其统治基础。事实上,不仅是罗马帝国时期,随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同样充斥着大量类似的例子,例如16世纪中期在英国出现的可减少劳力的拉绒机、织袜机,均遭到了行会的抗议以及统治者的立法阻挠。
弗雷对前工业化时期机械化失败提供了三种主要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劳动力比资本廉价得多,生产商没有动机去投资和发明昂贵的机器。从奴隶社会到后来的农奴社会,劳动力都是廉价甚至免费的,奴隶被比喻为前工业化时期的“机器人”。甚至有学者觉得,中世纪的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工人议价能力大幅度的提升,由此才促发了英国工业革命。
第二个解释是技术进步需要文化土壤,而这种文化土壤直到17世纪科学革命后才出现。前工业化时期流行的古典哲学思想与打造机器这些体力劳作的理念格格不入,古代宗教信仰也与科学和理性相矛盾。正如社会学家韦伯所指出的,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取代迷信文化是技术进步的关键,这种文化直到启蒙运动后才出现。[2]78
第三个解释,同时也是弗雷认为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统治者对于技术发展的态度。统治阶层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以及对于行会力量的忌惮,通常会阻止那些替代劳动力技术的应用推广。那么统治者的态度为何会在工业化前夕发生转变呢?以英国为例,首先,随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和商业团体的兴盛,王权受到了限制,政治权力从王室转移到了议会。发生在工业革命前约一百年的1688年光荣革命,推动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形成,并为打破政治和经济的保守主义铺平了道路。而另一方面,英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化使得地方性行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同行竞争导致地方性保护主义难以维系。政治力量的转移、国内外竞争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促使英国政府对待技术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意识到推广工业化、机械化可为其国际贸易带来非常大收益,而阻碍技术发展则可能没办法立足于竞争非常激烈的国际贸易环境。相对而言,机械化所引发的底层打工人的不满和动荡则退居其次。
如果说前工业化时期统治阶层通过政治手段阻碍技术的进步,那么工业革命前夕,统治阶层终于站在了推动技术进步的一方,技术由此开启了它影响工人命运的关键角色。弗雷在本书中讨论的“大分流”意指英国国家内部的大分流,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大分流。资本家利润上涨,但工人却工资停滞,收入不平等加剧。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工业化前期,工人的收入下降,生存境况每况愈下。[3]这种情形自工业革命初期一直延续到1840年,该时期也被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称为“恩格斯式停顿”。[2]132
弗雷认为这种情形与该时期大量使用的“劳动力替代型技术”(labour-replacing technology)紧密关联,这类技术通过机器和发明替代原本由工人手工完成的工作。例如,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可节约2/3的劳动力成本;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一样能节约劳动力,一名工人操作便可同时纺几条纱线;卡特赖特发明的动力织布机生产效率是手动织布机的40倍以上,一名织布工可同时操作18台机器,导致大量织布工人被淘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更恶劣的是,这些机器不仅剥夺了成年工人的工作机会,更催生了大量的童工。由于纺纱、织布等技能逐渐被机器弱化,以至于儿童也能轻轻松松完成这些工作,于是价格更低的童工取代了成年工人。书中引用的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19世纪30年代,英国纺织行业的劳动力约有一半为童工,煤矿行业则有约1/3为童工。[2]123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的“卢德运动”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卢德事件包括:1768年,500名锯木工人将伦敦第一座蒸汽动力的锯木厂焚烧毁坏;1772年,曼切斯特一家使用动力织布机的工厂被焚毁;1779年,兰开夏郡的几百名工人冲上街头表示要毁坏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机器;自1811年起,内德·卢德(Ned Ludd)①及其追随者们在英国中部工业重镇发动了至少100起破坏机器事件,破坏了约1000台机器。当时的英国政府对卢德分子的破坏行为采取了强力的态度:首先,议会在1769年通过法案,破坏机器者可被判处重罪甚至死刑;其次,英国政府对于工人骚乱事件更是直接出动军队。卢德运动最后无疑以失败告终——1812年至1813年间,超过30名卢德分子被处以绞刑。不仅是卢德分子失败了,另一些同样反对机器的温和的抗议者们,也没能通过游说和请愿的方式说服议会通过任何限制机器的法案。
1840年之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大分流开始略有弥合,工人的实际收入逐步增长,到1900年涨幅达到了123%。那么,为什么在工业化初期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到了1840年后反而开始增长呢?对此经济学家有多种解释,弗雷认为其中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技术革新的类型从“劳动力替代型”转变为了“劳动力增长型”(labor-augmenting),亦称“赋能型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随着蒸汽动力的应用和机械化的普及,机器也慢慢的变复杂,工厂开始需要越来越多懂得操作机器的技能工人,对工人技能要求的提升也通过工资的增长得以反映。此外,政府的干预也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收入状况。英国于1833年颁布了《工厂法案》,规定了上班时间,并且要求改善童工的工作条件和提高其工资待遇。因此,在法案颁布后的十几年间,童工的数量骤减。
如果说1840年之后的技术进步终于能够给工人带来些许福音,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以电气化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进一步促进了工人收入水平的增长,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近。经济史学家将1900—1970年这一时期称为“历史上最大的调平”。
对于“大调平”的证据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数据证据。从1870年到1980年间,美国工人的收入涨幅紧跟GDP涨幅,除“大萧条”时期,工人收入稳步增长,并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时,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此期间基本是下降趋势,并于70年代达到最低水平。而另一个间接的证据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几乎看不见卢德份子的抗议,说明工人对机器和技术进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意识到技术进步对于自身命运也是有利的,因此不再反抗机器。
工人态度转变的关键,在弗雷看来,归功于这一阶段的技术发明有着非常明显的“赋能”特征。也就是说,这些新的技术发明(以内燃机和电力为代表)不只是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任务、新的职位甚至新的产业,例如汽车、飞机、电话、电力机械、家用电器等现代制造业。一系列的新职位最重要的包含:工程师、机械师、维修工、后勤工人、经理等。这些新创造出来的工作增加了就业机会并且促进了新技能的形成。
不仅如此,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改变,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当美国家庭纷纷用上了家用电器后,大量的全职主妇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职场当中,成为受薪的办公室职员,于是便形成了当时独具特色的“粉领族”。正是上述职业群体构成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在弗雷看来,“技术本身让每一个人都从中获益,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中产阶级。”[2]145
无产阶级的命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被改写,除了技术革新的类型从“劳动力替代型”转变为“赋能型”,是否还存在其他社会、政治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呢?弗雷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合法化和福利体系的形成对此不无作用。但这些因素,在弗雷看来不如技术本身的作用来得更为关键。他认为工会的角色是有限的,如果工人们的技能很容易被技术取代,工会也将缺乏议价能力,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为工人谋求退路。而资本主义的福利体系,如早期福特汽车在企业内部推广的福利项目,以及后来实施的罗斯福新政,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也为失业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缓解了技术进步带来的阵痛。但是,弗雷并不赞同将长期的薪酬增长归功于福利体系,而认为工人薪酬的增长取决于其技能和知识对生产力的贡献。哪怕是在没有工会和政府干预的时期,只要生产力提高了,并且驱动生产力提高的技术本身是对工人赋能的,工人就可以实现收入增长。
“大反转”指向的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自动化与计算机时代,由大量中等技能工人构筑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没落,中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停滞甚至下降。那些未能通过高等教育获得足够应对高科技时代所需的技能和知识的劳动者,正在被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所淘汰。再一次,弗雷从技术的类型对此进行解释。他认为,以自动化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有别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机械化。机械化时期的机器设备需要依赖工人的操作,因此创造了大量的“机器操作工”岗位。但在自动化时代,由计算机所控制的自动化机器取代了机器操作工的角色,大量重复性的、常规性的工作任务(routine tasks)均可由计算机替代完成。从1979年至今,超过70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美国消失。
弗雷看待技术的观点与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en)的“去技能化”观点有所不同。布雷弗曼认为机械化是一个连贯的技术发展过程,包括半自动化和后期的全自动化。自机械控制工具出现之后的机械化过程均为去技能化,并且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升,工人被去技能化的程度不断加剧。[4]而弗雷则认为机械化技术是“赋能式”的,自动化技术才是“去技能化”的。在机械化阶段,工人需要掌握操作机器的技能,机器也需要依赖工人,尽管这些技能被布雷弗曼认为是不需要花费太多脑力的重复性劳动。但总的来说,弗雷与布雷弗曼对于自动化的判断是一致的,即自动化技术会导致工人的技能被削弱并且面临着技术性失业的危机。
当然,计算机的普及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如计算机程序员、机器人工程师、信号分析师等。但这种情形与机械化时期不同的是,这些工作几乎不会提供给大学以下学历的劳动者。于是,低学历的劳动者只能从高生产力的制造业流动到低成产力的服务业,如门卫、园丁、看护等职业。也因为这些服务性行业的“生产力天花板”太低了,无法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扩大利润,劳动者的工资也因此缺乏上涨的空间。这就是诸多经济学者所提出的“工作两极化”现象——高技能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的比例都上升了,但中等技能工作的占比却不断下降。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同时发生在欧洲国家。
既然这一轮的技术进步并不能普遍地让工人受益,那么工人是否会像19世纪的卢德分子那样激烈抗争呢?各国政府的应对姿态又如何?事实上,美国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表示支持限制机器人或自动化的政策以减少其对就业的影响。工人对机器的态度似乎重新回到了19世纪时的状态。然而,在现代法治体制下,工人不可能再像卢德分子那样通过暴力破坏机器和厂房的方式表达诉求,他们只能采取游说、投票等方式。弗雷认为,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抬头与此不无关系。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能够在竞选中获胜,正是因为获得了大量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因为这些工人相信,他们的工作要么被机器抢走,要么被中国抢走。[2]282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在酝酿或已经出台应对政策以减轻新一轮的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例如,韩国政府出台措施缩减了投资机器人和自动化的税收优惠;法国政府则通过了一项针对亚马逊的法例,禁止其线上售书免运费,以此来保障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和工作机会。弗雷担忧民粹主义会最终引向“技术恐惧型”政府的出现,但也有学者批评这种担忧缺乏证据。[5]
限制技术革新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全球化环境下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各国政府如果为了保证就业而停止技术改造,后果将是生产力落后于国外的同行竞争者,国家内部的政治不稳定则会转化为外部的威胁。正如书中引用的一名美国工会领袖的观点,“如果不自动化,就不只是丢掉工作,连工厂都要搬走。”[2]290不管是为了保证就业而限制技术的发展应用,还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罔顾技术对就业和工人的冲击,两种应对方式都显得捉襟见肘。事实上,技术进步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问题远不止失业,还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犯罪率上升、家庭婚姻瓦解、后工业地带服务业的衰落,等等。如此看来,技术的进步不仅没有带来凯恩斯所预期的美好前景——富足的生活和闲暇的时间,反而是留下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当今时代流行的新兴技术,如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等,在弗雷看来几乎都是“劳动力替代型”的。这些技术是否会加剧自动化时代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呢?面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新的挑战,是否存在破解之道?弗雷认为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如何将技术创造的较少的工作和巨大财富进行分配的问题。基于“再分配”的思路,弗雷讨论了若干种可能的应对策略,例如教育、再培训、工资保险、税收抵免、人口迁移、扩大住房供应、加强城市间交通连接、复兴工业等。下面选取其中较具借鉴意义的四种加以介绍。
一是教育。历史经验证明教育的扩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教育既为技术进步提供优秀的研发人员,又为新产业或新技能岗位提供人力资源。事实证明,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们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相对较低。尽管低技能的工作还被社会所需要,但这些岗位未来面临着更高的被取代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教育政策同样面临挑战:那些来自弱势家庭背景的孩子在教育上的表现相对较差,而弱势背景的孩子也许正是来自于那些因自动化而失业、降薪、家庭破碎的工人家庭。如此看来,教育系统如何让资源均等化,保障不同背景孩子的教育获得,是下一代免受新技术淘汰的必要机制。
二是再培训。对技术性失业群体提供再培训曾经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应对自动化焦虑的一个国家方案。但这种高投入、大规模培训的效果却难以评估。作者提倡的是另外一种再培训的思路,即通过税费返还的方式激励低收入群体自选培训课程进行自我投资。不管是国家投资的再培训项目,还是自我投资的再培训课程,弗雷认为应对快速的技术革新,“终生学习”的概念值得提倡,如此才能满足不同职业阶段的技能需求。
三是工资保险。因技术性失业的工人,尽管最后仍能找到其他的工作,但工资几乎都会下降。工资保险的作用就是为了保障那些因自动化而被不得不接受薪资较低工作的工人的收入。这一保险目前在美国仅用于保障受到进口贸易影响的50岁以上、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工人。弗雷认为这类方案可扩大应用到受自动化影响而降薪的工人群体。
四是税收抵免。弗雷不赞同现在被广泛推崇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方案。他认为若人人均能享有基本收入,那么不管工作与否、贫富与否,均能获得同样的收入保障,这种再分配机制本身就会加剧不平等。相较而言,弗雷更支持另一种“工作者税收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的方案。此种方案可为低收入的工作人士提供税收抵免,也被验证可以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并且激励人们重返职场。弗雷认为这种税收抵免的方案可以扩大使用,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的有孩子的家庭更应给予类似的补贴。[2]357税收抵免可能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更具可行性的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弗雷对于UBI的评价是有失偏颇,存在着性别盲点,并且未能区分“受薪工作”与“无薪劳动”(如家务劳动)之间的区别。[6]
弗雷提出的若干种应对策略,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有助于修复社会问题的较具可行性的政策建议。然而,弗雷的建议相对短视,并且显现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即认为个体应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知识技能水平以应对技术进步的挑战。对此,未来学家马丁·福特(Martin Ford)认为,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和职业培训)和税收调整只是短期的措施,长期而言,应该让任何一个人都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让人人成为资本家。[7]但这恐已超出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文将就全书的局限性进行评述,并尝试探讨应对技术陷阱的另类路径。
弗雷在本书中的核心观点是,技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人的命运,而技术进步的类型则决定了工人命运的走向。他将工业化时期的技术进步区分为两种类型:劳动力替代型和赋能型。前者的效果是节约劳动力、替代劳动力,后者尽管也能起到节约劳动力的作用,但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者的技能提升,来提升其劳动回报。弗雷在书中列举了一些劳动力替代型技术,如动力纺织机、自动电梯、机器人技术;而赋能型技术则包括电气化时代的各种机械技术,以及计算机时代的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等。尽管弗雷看到了不同技术对工人命运的影响,同时也承认政治、经济因素在调节技术影响时发挥的一定作用,但从该书的整体论调来看,弗雷依然是一位隐藏的“技术决定论”者,这大多数表现如下两方面。
首先,弗雷是依据技术产生的影响效果对其进行类别界定的,但具体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技术的发展路径,技术为何会发展为替代型或赋能型,弗雷对此并无解释,仿佛这是技术的自身规律,我们只可以在事后进行考察和评价。正如一评论者所言,弗雷将技术的变革放置在政治论争之外。[8]事实上,美国工业社会史学者戴维·诺布尔(David Noble)的研究也证明了技术怎么样发展并非基于其自身的规律,资本和政府在影响机器设计的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自动化的技术选择上,决策者们最终选择了对工人去技能化的“数值控制技术”,而非另一种需要依赖熟练技术工人的“记录-回放”技术。[9]而德国的自动化经验也说明人类能选择另一种技术发展路径——放弃高度自动化的、以机械系统为中心的设计,选择了一种在生产流程中以人为中心的路径,如小组作业、机床的厂内编程、以及让员工参与自动化解决方案的构造和实施。[10]可见,弗雷对于技术进步的观点存在着技术决定论者的视野盲点。
其次,弗雷在书中屡次提到,决定工人收入状况的关键是由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改变,而政策、经济、社会因素尽管不无影响,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其理由是英国政府在20世纪初才引入最低工资保障,而工会覆盖率在19世纪下半叶都非常低,但那一段时间工资却持续增长。因此,他认为工资增长(或不增长)最好的解释就是工业化过程本身。美国经济史学家乔·默基尔(Joel Mokyr)对弗雷的解释表示质疑,他指出1850年之前工人收入增长停滞、生活水准下降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如人口的迅速增加、农业欠收、《济贫法》的废除、战争及随后的经济萧条等等。[5]
这种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在对“大反转”进行解释的时候尤为明显。尽管或多或少提及了全球化、自由贸易对不平等加剧的影响,但弗雷认为自动化技术的角色被轻视了。他引用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的观点试图证明全球化只是人们攻击的靶子,技术才是线但正如评论家莱姆·肯尼迪(Liam Kennedy)所言,弗雷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深入考察。这场始于里根、撒切尔上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了一些系列让工人力量削弱和利益受损的举措,如福利体系的瓦解、打压工会的立法、自由贸易和离岸外包导致的制造业衰落等。[11]因此,“大反转”的出现并非单纯的由技术革新的方式所导致,而是由全球性的政治经济转型及受其影响的技术革新路径所综合导致的结果。
总而言之,弗雷的解释将各时期影响工作、工资的复杂因素单一化,同时也轻视了政府干预和工会运动对技术影响的调节功能。弗雷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位隐藏的技术决定论者,又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应该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来解决——通过政府干预对有限的工作和巨大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但如果工作的变迁和工人的命运由技术的本质所决定,那又怎么样确定政府干预能够产生期待的效果呢?弗雷的这一倾向与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同类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12]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后者被批评缺乏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讨论,且具有“技术拜物教”的倾向;[13]弗雷虽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补充了后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不足,但在“技术拜物教”这一倾向上却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弗雷只看到了技术作为一门政治经济学的其中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财富是如何产出的。忽视了生产的领域而只关注再分配领域,导致弗雷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只能是在既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框架之下的“修补式”的应对之策。事实上,技术进步带来的问题,早已潜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当中。技术本身就是权力不平等的产物,它被发明出来的目的正是为资本攫取更大的利润;那些不能促进生产力和削减劳动力的技术往往不会被资本家所采用。[13]要直面问题的本质,则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回到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去讨论机器与人的关系,回到生产关系中去审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在技术变迁过程中不断演变,同时反思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怎么样影响技术的发展路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颇有洞见,他们呼吁去除技术拜物教,加强政府对数字时代工人权益的立法保护,[13]更进一步的是,加强技术的集体所有性,抵御资本主义式的人工智能,发展一种“导向的人工智能”。[14]
尽管《技术陷阱》一书留给读者许多疑问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工业社会史的优秀著作,为读者详实地展示了历史进程中的技术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和工人命运的广泛关联。该书的政治态度相对中立,其提出的政策建议也较容易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接纳,对于我国政府评估和调节技术发展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88-447.
哈里·布雷弗曼. 劳动与垄断资本: 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 方生, 朱基俊, 吴忆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 163-210.
马丁·福特. 机器人时代: 技术、工作与经济的未来. 王吉美, 牛筱萌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286-312.
戴维·诺布尔. 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李风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95-226.
阿尔冯斯·波特霍夫, 恩斯特·哈特曼. 工业4.0: 开启未来工业的新模式、新策略和新思维. 刘欣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61−62.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安德鲁·麦卡菲. 第二次机器革命. 蒋永军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胡万亨. 当卡尔·马克思遇见人工智能——《非人的力量: AI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评介. 科学与社会, 2021, 11(2): 123-13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智能制造趋势下的劳动体制变迁研究”(19BSH086)。